狮子与太阳——萨法维王朝的兴衰(三)伊朗人与什叶派
对于新成立的萨法维王朝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国家系统。作为前身的萨法维教团,并没有实际管理过任何地区。因此,最初的萨法维王朝基本全盘吸收了白羊王朝的国家机构。在此基础上,由于红头部落在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作为回报,这些部落的埃米尔、贵族和士兵在新国家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萨法维王朝的行省分为两种,王室行省( khassa)与国有行省( mamalik)。前者属于中央直辖,由王室派遣官员管理,而后者的总督则由各红头部落埃米尔担任,大都终身任职,家族世袭和父死子继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根据部落传统, 伊斯迈尔实行“提尤尔( tiyul)”的土地制度, 把大量土地分封给这些部落作为军事封邑,除了将维持封地和供养自己以外所剩余的一点税收盈余供奉给中央和为国王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外,部落埃米尔们在其封地上拥有行政、军事、税收和司法大权。萨法维家族还与重要的红头部落间进行通婚,进一步提升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王室本身缺乏军事力量的弱点,伊斯迈尔从各个红头部落中抽调年轻精锐,组成了3000人的王室直属禁军“库尔奇(Qurchi)”,这个名字来源于蒙古语,本意为“持弓者”,他们的薪水从王室收入中调拨,只听从沙汗沙的命令。
也是在这个阶段,伊朗本土的书吏阶级(Dabiran)开始登上萨法维王朝的舞台。书吏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便已出现,原本是对负责拟定各种文件,监督地方执行的官员的代称。而到了萨珊王朝时期,书吏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了种姓之一。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的记载,萨珊的贵族阶级分为三等:一为祭司,二为武士,三为书吏。这三个等级都是特权阶级,不需要缴税。阿拉伯大入侵之后,前两个阶级都随着琐罗亚斯德教的衰退逐渐消亡,但书吏们却迎来了真正的高峰。哈里发们借鉴了萨珊王朝的政治体制,而书吏成为了哈里发政权行政体系的核心。这一点也被之后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所效法。
实际上,在沙鲁尔之战开始之前,原白羊王朝的维齐尔,穆罕默德·扎卡里亚·库朱吉(Muhammad Zakariya Kujuji)就投靠了伊斯迈尔,他的祖先从帖木儿帝国时期就服务于伊朗的统治者们。默罕默德向伊斯迈尔透露了许多白羊王朝内部混乱的情报,建议伊斯迈尔抓住时机发起进攻,因此得到重用,成为了萨法维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大维齐尔。此后,他为萨法维王朝培养了许多行政官员,他的儿子贾拉尔(Jalal al-Din Mohammad Tabrizi)后来也担任了大维齐尔。除此之外,曾经为乌尊·哈桑和叶尔孤白服务的萨夫吉家族(Savji Family)的多名成员被伊斯迈尔任命为阿拉伯-伊拉克、呼罗珊以及大不里士的教法官。伊斯法罕的贾比里家族(Jabiri Famliy)担任法尔斯的维齐尔执掌当地的行政大权,其在法尔斯的显赫地位贯穿整个萨法维王朝。
伊斯迈尔对伊朗书吏的重用,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伊朗文官相比于红头埃米尔们更熟悉伊朗内部的政务运行;另一方面,书吏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法对伊斯迈尔的统治造成实质威胁,更方便控制。此后伊朗书吏借由沙汗沙的支持逐渐发展为一股可以与红头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两者也因其特性而被称为执笔贵族(men of the pen)与执剑贵族(men of the sword)。双方都视对方为眼中钉:书吏认为红头是不懂吟诗作赋的莽夫,而红头则当书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萨法维王朝初期最重要的几个职务都由两个集团分别把持。负责军务的大埃米尔(Amir al-umara)和禁军指挥官库尔奇巴什(Qurchi-bashi)由红头出任,而负责政务的大维齐尔(Vazīr-e Azam)以及负责教务的萨德尔(Sadr)则都是伊朗书吏。除此之外,伊斯迈尔还在1501年创造了一个新的职务——瓦基勒(Vakil),作为自己的权威代言人,总领军、政、教三方事务。萨法维王朝历史上第一位瓦基勒是侯赛因·贝格·拉拉·沙姆鲁(Husayn Beg Lala Shamlu),他是当年营救阿里以及保护年幼的伊斯迈尔的七人(ahl-i ikhtisas)之一,在红头中德高望重,原本担任大埃米尔之职。但在其任职6年之后,便被伊斯迈尔罢免,改为伊朗人阿米尔·纳贾姆(Amir Najm)。至此之后伊斯迈尔任命的瓦基勒基本都是伊朗人,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伊斯迈尔对红头们的猜忌日益加剧,试图用伊朗书吏对其进行压制。
在处理国家政务的同时,伊斯迈尔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宗教。伊斯迈尔统治下的人民,大多数属于逊尼派,首都大不里士超过2/3的人口是逊尼派穆斯林。而萨法维教团,是一个混杂了多种宗教的苏菲教团,教义更多是体现出一种狂热,可以用来蛊惑人心,但对统治国家并无益处,特别是一些红头军中的极端分子,他们视伊斯迈尔为神和先知,但也会高喊着伊斯迈尔的名字劫掠伊朗的城镇。伊斯迈尔以抢劫和谋杀的罪名处死了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则被送往安纳托利亚,交给当地的萨法维教团代理人,继续按照原来教团的方式进行管理,在奥斯曼帝国的腹地抢劫村庄,袭击军队,制造混乱。但在国内,为了能更有效的控制住红头军,回归“正统”信仰,就成为了伊斯迈尔的首要任务。他并没有改信逊尼派,而是选择了伊朗地区的少数派——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作为自己国家的官方信仰。他的幕僚们都劝谏他再考虑一下,避免引发民变。但伊斯迈尔力排众议,在第二天的呼图白上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要在日后的聚礼祷文中加入什叶派清真言“阿里是真主之友”。红头士兵按照伊斯迈尔的要求混迹在人群之中,对于任何反对者及有异动的可疑分子都直接擒拿。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伊斯迈尔开始用“铁与血”的方式,在自己的国度内强行推广什叶派。
首先,对于普通的逊尼派信众,伊斯迈尔使用胁迫的方式逼人们改信什叶派,不从者将被处以死刑。他曾说过:“真主和不谬的伊玛目在我左右,我无所畏惧。如果有人敢说一个反抗的字眼,我必拔剑相向,毫不留情。”此后的事实证明,伊斯迈尔的确说到做到。他摧毁逊尼派的清真寺,对逊尼派乌里玛或监禁或处死。对敢于抵抗的人,迎接他们的将是萨法维军队的血腥镇压。在占领巴格达、赫拉特的过程中,伊斯迈尔都对城内不肯改信的逊尼派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他还将对三位“簒夺者”(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的诅咒和侮辱加入到宗教仪式中,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节日以庆祝欧麦尔遭到“天罚”(欧麦尔在公元644年被波斯奴隶刺杀身亡)。在那一天,群众们会举着一个代表欧麦尔的人偶游街,途中会对“欧麦尔”进行谩骂并投掷石块,最后烧掉人偶,开始狂欢活动。有史以来第一次,逊尼派成为了被歧视迫害的一方,大量的逊尼派穆斯林逃亡安纳托利亚、河中和南亚次大陆。其行径甚至引来了邻国的不满。曾经祝贺伊斯迈尔战胜白羊王朝的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以一位长者的身份,“规劝”伊斯迈尔适可而止,但遭到他的无视。1511-1512年期间曾在伊朗游历的葡萄牙人Tomé Pires在提到伊斯迈尔时指出:“他(即伊斯迈尔)改造了我们的教堂,摧毁了所有追随穆罕默德(的圣训)的摩尔人的房屋……。”
其次,伊斯迈尔开始对遍布伊朗的各个苏菲教团展开大清洗。虽然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他和部分苏菲教团达成了妥协,但对大部分的教团他都采取了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他下令消灭苏菲教团的传系,铲除已故苏菲长老的墓地。活跃于阿塞拜疆的逊尼派苏菲教团哈尔瓦提教团,原本在白羊王朝的庇护兴旺起来,因这一层亲密关系而受到萨法维王朝的猜忌。在伊斯迈尔宣布以什叶派为国教时,该教团的谢赫易卜拉欣·古尔沙尼(Ibrahim Gulshani)立刻离开了大不里士,其信徒也大多逃往奥斯曼,其在伊朗西北部的势力被连根拔除。在占据法尔斯之后,伊斯迈尔对当地的阿布·伊沙·卡兹鲁尼(Abu Ishaq Kaziruni)教团进行了镇压,约有4000人被杀,所有苏菲长老的陵墓被摧毁。1510年,伊斯迈尔又驱逐了赫拉特有名的苏菲教团——纳克什班迪教团,神秘主义者喀什格哈里(Kashghari)和加米(Jami)的墓地都未能幸免。该教团在伊朗的影响被完全根绝。
最后,就是对什叶派“异端”的处理。为了树立十二伊玛目派的权威,萨法维王朝对什叶派的其他支派严加管控。比如七伊玛目派的支派尼扎尔派原本在伊朗很有影响力,以刺客而闻名于世的阿萨辛就是由尼扎尔派中的极端分子组成。1510年,尼扎尔派伊玛目塔希尔(Tahir)准备前往卡尚担任教职,他的追随者纷纷前往该地,这引起了伊斯迈尔的猜忌,下令处死他。塔希尔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夜逃去了印度,从此再未能回到伊朗。
为了加强十二伊玛目派的国教地位以及传教的执行力度,伊斯迈尔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来负责宗教行政事务、特别是对教产瓦克夫(Waqf)的管理和对沙里亚(al—Shari‘ah)的维护宣传,铲除异教徒和逊尼派也是他们的职责,有时也会担任军职,这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萨德尔。另外由于伊朗本地什叶派的稀少,真正了解什叶派基本教义的人寥寥无几,连可供参考的什叶派教义学著作,也是四处难寻。伊斯迈尔曾搜遍了大不里士全城,才从一位教法官的家中找到一本圣贤希里(Allamah Al-Hilli,1250-1325,十二伊玛目派的教法学者、穆智台希德)的著作,还只有第一卷。萨法维教团之中,红头军对什叶派教义基本一窍不通,而教士们也没受过正规的教法教育,伊斯迈尔只好派人前往伊拉克、黎巴嫩和巴林聘请什叶派乌里玛,来协助建立新的宗教体制。不过,大多数的乌里玛都没有响应。对一个什叶派教法学者而言,只有隐遁伊玛目复临才能在大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什叶派国家。在大隐遁期,只有穆智台希德才能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判断,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代替隐遁伊玛目进行统治。而自称是神,还无视教义公开饮酒的伊斯迈尔,是个毫无疑问的“异端分子”,他们不愿向伊斯迈尔低头(萨法维宫廷实行东方式的跪拜礼)。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如果答应了萨法维王朝的邀请,会遭到本地逊尼派统治者的报复。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坚定,一部分人很难拒绝这一机会。能在一个国家中推广什叶派,对于有抱负,想要将什叶派发扬光大的乌里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些学者来到伊朗,给伊朗的宗教体系以及阿拉伯语在伊朗宗教生活中的应用产生了巨大影响。阿里·卡拉奇 ( Ali al-Karaki) 是这些早期什叶派移民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他在日后被塔赫马斯普封为“封印穆智台希德”,萨法维王朝的最高宗教权威。
新建立的什叶派体系,不仅强调穆斯林必须履行的礼拜、斋戒、朝觐等宗教义务,还通过宗教仪式等具体宗教行为强调什叶派的一些特殊因素,并将之制度化。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素材。早在萨法维王朝之前,英雄受难、殉教牺牲的激情在伊朗人中就很有影响。大约10世纪时,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开始举行阿舒拉日的纪念活动。到萨法维王朝,讲述侯赛因的殉教故事和举行公共悼念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在公共悼念活动中,人们无论老幼尊卑一起出动,为侯赛因所遭受的苦难而恸哭。更有人不断以刀剑击打自己的身体,直至鲜血淋漓,借此表达对伊玛目的热爱。与此同时,对什叶派伊玛目圣墓的朝拜,也逐渐流行开来,并形成惯例。
另外,伊斯迈尔还在自己的血统上做起了文章。他宣称自己的先祖是第七伊玛目穆萨·卡兹姆 ( Musa al-Kazim)的后裔,而自己是隐遁伊玛目的化身,具有不谬性,以此来强化王室的神圣性和正统性。当然,这种做法是与正统什叶派教义背道而驰的,不过此时的什叶派太过弱小,必须仰仗王权的支持,所以乌里玛们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萨法维家族的圣裔系谱及传说从伊斯迈尔开始提出,到其子塔赫马斯普时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虽然当时的伊朗人大多是逊尼派,但对阿里及其后裔普遍都怀有一种同情及尊敬,特别是第四伊玛目的母亲是萨珊王朝的末代公主,对于崇尚“高贵血脉”的伊朗人而言很具有亲和性。这可能也是伊斯迈尔选择十二伊玛目派的原因之一。
通过与十二伊玛目派乌里玛的合作,伊斯迈尔完成了对伊朗什叶派体系的框架构建,萨法维家族成为了“新什叶派”的核心。伊斯迈尔的举动成功将伊朗与逊尼派的奥斯曼、乌兹别克人割裂开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年伊尔汗国的尴尬处境。虽然其内在仍存在严重的苏菲主义残余,但也为日后什叶派在伊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到这一刻,所有的事情都还是按照伊斯迈尔所预期的方向在发展。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原本并不怎么在意的东北方,成为了最先崩溃的一环。
参考书目资料:
《Iran under the Safavids》,Roger Savo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ume 6: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s》,Peter Jackson
《伊朗伊斯兰教史》,王宇洁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
《萨法维王朝时期土库曼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贺婷
《论萨非王朝政治体制中的国王、部落和乌里玛》,雷昌伟
《萨法维王朝对外交往研究》,王平
《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李铁匠
《浅论伊朗古代书吏制的政治文化价值》,陆怡娜
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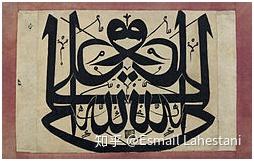

2 条评论